熱門資訊> 正文
艾米莉·狄金森:最終,勞作者與嬉遊者將同歸於無形
2023-03-19 10:32
【編者按】
現代主義詩歌先驅之一、美國傳奇女詩人艾米莉·狄金森生前更為人所知的身份是園丁。這位以隱居避世著稱的詩人,交往僅限於「友人和花」,其三分之一以上的詩歌及近一半的信件都提到了她最喜歡的花,花既是她詩歌創作的繆斯,亦是她一生珍愛的夥伴。在《狄金森的花園》一書中,作者朱迪絲·法爾引用了大量一手資料研究狄金森詩作與生平。她以花朵、園藝為切入點,對狄金森的氣質、審美,以及她看待藝術與自然之間關係的方式提出了新的看法。法爾將狄金森的花園之愛置於當時的文化語境之中,描述其起源、發展及與其家族喜好的關聯,思考狄金森花園的建構與數百首詩歌和詩性書信的對應關係。本文摘自該書《尾聲·園丁四季》,澎湃新聞經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授權發佈。
對於艾米莉·狄金森來説,春天就是光明,在真實與象徵的雙重意義上皆如此。她筆下的三月,如同藝術上的對手——他的功績,讓她渴望,卻又永遠無法匹敵,因為原初的色彩只屬於他一人:「那重疊小山你留我着色-/卻找不到恰切的紫-/已全部被你帶走。」重要的語詞「紫」又一次出現,它象徵着尊嚴、地位、才華與聖潔。夾在嚴酷冬季與温暖春天之間,三月令她驚喜。她以沉潛的才華創造出了無限廣大的魔幻世界,山間的光影彷彿熙熙攘攘的人羣,「東方」與「西方」是每天抬着太陽出入「白日」大門的巨人,春天則成了神奇的靈藥。她用家庭主婦的形象來描述它:「用你灰白的活計搭建好我的心/然后請在這玫紅的椅上安坐-」她帶着狂喜與春天邂逅:「我遇到春天時-按捺不住感動-/心中溢出古早的想望-」冬天「灰白」,春日「玫紅」,各有獨特的顏色:冬天寒霜灰白,春日枝頭莖上花蕾玫紅。狄金森筆下對春日的渴望,幾乎無可匹敵。
因此,也許其中摻雜着些許恐懼。因為她需要春天來喚醒她照料的花園——花園是重要的詩歌主題——所以她擔心,有朝一日,春天不再到來:
當五月到來,若五月迴轉,
難道無人擔憂
如此華美容顏
他卻無法重睹?
在艾米莉·狄金森心中,春天還有其他更為私人化的意義。她曾對伊麗莎白·霍蘭剖白心跡:「某些特別的月份似乎既施予又剝奪-八月施予最多-四月-剝奪最多-循環反覆,永無盡頭。」在另一封致霍蘭夫人的信中,她又説:「愛的日期只有一個-‘四月一日’,‘今天,昨天,以及永遠’-」在內戰中,查爾斯·沃茲沃思同情南方,1862年4月他被迫離開費城的拱門街(ArchStreet)長老會教堂,遠赴舊金山。二十年后的4月1日,他去世了。狄金森的書信本身、隨信附贈花朵的指涉以及信中徵引的兩行丁尼生詩句(據托馬斯·約翰遜考證,第一句引自「悼念」,第二句引自「愛與職責」,看上去都像是確認沃茲沃思為「大師」的鐵證。但是狄金森常會將獨特的愛意與非凡的讚美慷慨賦予朋友,而這些朋友並不見得是她所「愛上」的人。語詞的力度,與情感的力度一樣,對她來説不可或缺。沃茲沃思1880年8月拜訪過艾米莉,而且二人可能早在1861年夏季就已見過面。這同樣會令人覺得他就是「大師」。但是不要忘記,塞繆爾·鮑爾斯1862年4月5日啟航去了英格蘭。狄金森在寫給瑪麗·鮑爾斯的一張便條里,提到了塞繆爾的離去。便條中那滿溢的慾望與痛苦,彷彿鮑爾斯已然逝去:「最好的已然離去-其他一切便無關緊要-心只求其所欲……見不到你我所愛,太可怕。」
黃水仙、山谷百合、牡丹、番紅花等鮮花復甦的季節,也是她重嘗苦澀之時。春天的「激流」「拓開了每個靈魂-」。在狄金森眼中,春天如同聖典。「激流」—春雨—就是一種洗禮,聖靈神力的直接啟示。春日花園令她窺見了上帝:
春天這個時節
上帝親自送達-
與其他季節一同
他居住其中
到了三月四月
外面仍無精打采
除非同上帝
來場親密交談-
艾米莉·狄金森所信仰的上帝全在詩中。她的上帝自1860年以來就已在某種程度上與花園融爲了一體。「外面」指的主要是她父親的土地。對她而言,所有的季節都由神意點染,但春天與衆不同,它直接證明着上帝的存在與善意。如果花能與人交流,那麼每年春天百花復甦便是它們與造物主愉快的「親密交談」。
在狄金森出生的一百多年以前,另一位馬薩諸塞州的作家也曾將靈魂比喻成「上帝的花園」。他同樣熟悉「林中的隱祕之地」,也有一塊能夠思索自然神性的「退守之地」——他就是喬納森·愛德華茲(Jonathan Edwards),一位清教牧師兼詩人。在《私人敍事》(Personal Narrative)中,他為皈依的基督徒靈魂尋找到了頗為雅緻的比喻:「如同每年春天我們見到的白色小花,謙卑地緊貼土地,盛開的花朵喜悦地沐浴着太陽的光輝,不動聲色地經歷着幸福的狂歡,馨香四溢。」愛德華茲的白色小花,也如狄金森最愛的銀蓮花一樣,「可愛,……謙卑,心靈殘損,靈魂柔弱」。在他看來,這些小花是美德的典範:「沒有什麼(比它們的品質)更讓我渴望。」這些謙卑美麗的春日小花終令他相信了「耶穌基督的親切與美」。(相信小花在藝術上具有優越性的約翰·羅斯金,是否曾讀過喬納森·愛德華茲的文字呢?)艾米莉·狄金森不會如愛德華茲一樣,將這些小花對應為三位一體中教導信眾「像小孩子一樣承受神國」的聖子。但對狄金森和愛德華茲二人來説,春天都點燃了他們「內心深處的火種」。如同愛德華茲,狄金森也會大膽地相信,鮮花的復甦或許就昭示着她自己的復活。
艾米莉·狄金森自稱「清教徒」時,她心中想的是自己的「清教徒花園」,這或許並非偶然。這個短語她寫於冬日落雪之后,但寫作時間並不足以解釋這一巧合。瞭解狄金森的讀者絕不會將她熾烈的情感與清教徒古板的教條相連。她所謂「清教徒」,可能更多地指向純淨、潔白之意。因此,她會邀請詹姆斯·S.庫珀夫人:「你該來……看看我的房子,大自然將它粉刷得如此潔白,問都沒問我-大自然很‘老派’,説不定是個清教徒-」狄金森關於白色的觀感與愛德華茲頗為相似,並不侷限於白雪之白,更指向內心純潔。花園會激發神聖之情:
花的善意
人若想擁有
必要首先出示
蓋印的神聖許可
春天與清新、純潔、神聖緊密相連,那夏天是怎樣的呢?狄金森的夏日圖景有趣又複雜,或許可以概括為果實成熟的完美喜悦,以及靈魂與花園繁花盛放的凱旋:
我的花園-如同海灘-
緊鄰着-大海-
夏天來臨-
宛如-她拾得的
珍珠-宛如我
這首詩仍按慣例有花為伴,花就是她園中的「珍珠」。在「舉足輕重的一生」一詩中,幾乎可以斷定珍珠指的就是蘇珊·狄金森——典出狄金森最愛的《馬太福音》中「昂貴的珍珠」一語,以珍珠寓喻靈魂。「珍珠」一詞的精神指涉常令她感動。她的園中之花宛如珍珠,這更加深了花朵的神聖意味。而大海意象,一如「東方」,複雜多變,象徵着永恆、痛苦、熱情或包容大地的遼闊天空。在本詩中,夏天情境中的大海不再咄咄逼人,而是成了巨大簡朴的珠寶盒子,內中藏着快樂。「我的花園-如同海灘」這樣的小詩,常有一種未完成之美,彷彿需要隨信附贈的鮮花來補全。無論是意義,還是結構,這樣的小詩當然比不上那些常被選入集子的精美詩篇,比如「靈魂時常傷痕累累」或「青銅-火焰-」。它們是詩歌便條,文學價值或高或低,但狄金森常會用這些小詩補全鮮花或禮物的未盡之意,反之亦然。詩與花,聯結起了她的雙重使命:詩人與園丁。
狄金森最為畫意沛然的一首詠夏詩,形容「蝴蝶/如門內美人」,破繭而出,撐着斑斕的陽傘,在草地上游樂直到黃昏。蝴蝶可不是草地上收割草料的農民,它們「迷失於外面/炫人耳目的誘惑」,「四處修修補補-/杳無規劃」,似乎總在「漫無目的地悠遊」。狄金森將這首詩稱為「熱帶表演」(重點為筆者所加),用上了她內涵豐富的形容詞。比起「辛勞的」蜜蜂與「熱情滿溢的」鮮花,蝴蝶與其他「夥伴-像她一樣的魅影-」都是圍觀勞作者的「閒散看客」。狄金森或許很清楚,在西方藝術中,蝴蝶一直是靈魂的傳統象徵;在她的詩中,固然潛伏着某種愛默生式的正統觀念(「漫無目的」「杳無規劃」),但與之相抗衡的,卻是詩中人對蝴蝶優遊閒散生活的由衷欣賞。蝴蝶的漫不經心,「三葉草-懂得」。讀者能夠感受到勞作與玩樂間的衝突——這主宰了狄金森精神世界的衝突。最終,勞作者與嬉遊者皆會同歸於無形,那個午后也終將如蝴蝶般逝去,而詩中人會發覺:
直至日落潛行-穩步而來的潮-
收割乾草的人們-
午后-蝴蝶-
都將消逝-於海-
這幅夏日速寫中潛藏着某種黑暗。午后強光屈服於落日余暉,在這「穩步而來的潮」中,詩人目之所及的一切終歸「消逝」。18世紀的讚美詩,如伊薩克·沃茨(IsaacWatts)的「上帝啊,我們古老的救主」(「OGod,ourhelpinagespast」,1712)會寫到永恆的浪潮終將帶走一代代子孫,給原本歡快、明朗的畫面染上一層憂傷的悲光。但我們並不打算將這一傳統加諸本詩中的蝴蝶消逝,畢竟蝴蝶之死亦是重歸自然。「消逝」雖然迫不得已,但也可説是主動選擇——完滿而充實地度過一天、一生,之后走向終點。儘管光焰熄滅——這並不是個積極樂觀的意象,因為狄金森總是夢想着「死亡之后,精魄長存」——但它亦與勞作者一樣,同歸永恆之海,經由一條更為輕捷的彼岸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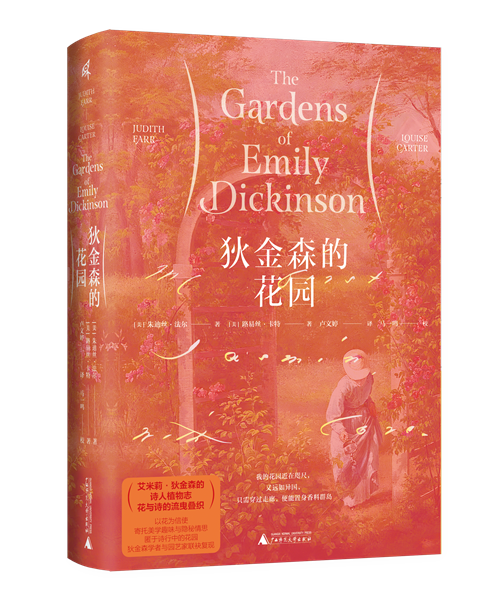
《狄金森的花園》,[美]朱迪絲·法爾、[美]路易絲·卡特著,盧文婷譯,新民説|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3年1月。
推薦文章
美股機會日報 | 阿里發佈千問3.5!性能媲美Gemini 3;馬斯克稱Cybercab將於4月開始生產
港股周報 | 中國大模型「春節檔」打響!智譜周漲超138%;鉅虧超230億!美團周內重挫超10%
一周財經日曆 | 港美股迎「春節+總統日」雙假期!萬億零售巨頭沃爾瑪將發財報
一周IPO | 賺錢效應持續火熱!年內24只上市新股「0」破發;「圖模融合第一股」海致科技首日飆漲逾242%
從軟件到房地產,美國多板塊陷入AI恐慌拋售潮
Meta計劃為智能眼鏡添加人臉識別技術
危機四伏,市場卻似乎毫不在意
財報前瞻 | 英偉達Q4財報放榜在即!高盛、瑞銀預計將大超預期,兩大關鍵催化將帶來意外驚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