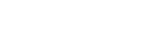热门资讯> 正文
夜读 | 巴菲特1990年在斯坦福法学院的传授:想赚大钱?专心“桶里捞鱼”
2025-12-10 23:59
沃伦·巴菲特执掌伯克希尔最后任期进入倒计时。
回顾他的投资分享,在那些精彩纷呈的股东信、公开演讲对话之外,其实有一堂被低估的课程。
1990年3月,巴菲特在斯坦福法学院上过一场客座课,这门课名为《每个律师都应该懂的商业常识》,是来自查理·芒格的构思。芒格还为此捐资在斯坦福设立讲席,并协助挑选了自己的哈佛法学院同学威廉·格里克巴格(William Glikbarg)担任授课教师。
巴菲特开场就告诉学生:商业和投资不是两件事,而是一件事的两面。你越懂企业的赚钱方式,就越知道什么值得投资;你越理解投资原则,就越能看清企业的本质。
他几十年经验背后的底层逻辑,表达成一句极简的话:画出你的能力圈,然后待在里面。
这堂课的内容涉及话题非常丰富。
比如能力圈。
巴菲特讲起95岁仍在为他工作的布卢姆金夫人,500美元起步做起一家年赚1700万美元的家具店。她不识字,也不懂会计,却靠一条原则无往不利:只做自己懂的事。能力圈的边界,她踩得比绝大多数MBA都准。
比如,为什么大公司常做糟糕的收购。
巴菲特认为,许多CEO升上高位,是因为在销售、运营等领域表现出色,但从未真正学过资本配置。一旦离开熟悉领域,只能依赖参谋部门或投行,判断力自然下降,收购质量也就难以保证。
比如为什么好的投资机会并不多。
巴菲特说,如果你的人生只有20次投资机会,你反而会做得更好。因为真正重要的,不是做多少决策,而是做少量正确的决策。这种“少做一点”的纪律,与华尔街“多做一点”的文化永远相反,却恰恰解释了伯克希尔几十年如一日的稳定表现。
三十多年过去,再读那天的课堂内容,会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这些原则从未被时间磨损,反而显得比今天的市场更清醒。
好在有当年的《杰出投资者文摘》(Outstanding Investor Digest)的记录(虽不完整,但保持了关键内容原汁原味的表达),我们今天才能重读这一段几乎被埋没的讲授。无以伦比的赞美!
以下是聪明投资者(ID: Capital-nature )的精译整理,分享给大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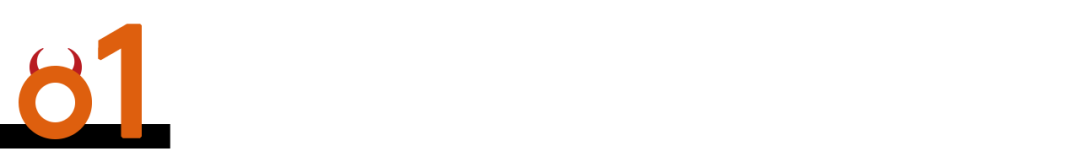
商业与投资,是一体两面的事
今天我们聊聊商业与投资。很多人觉得这两个领域毫不相干。但其实它们之间有很多共同之处,相互影响。
你越懂投资,就越懂如何经营企业;你越了解企业运作,就越能做好投资。
我很幸运,这么多年一直同时站在这两个领域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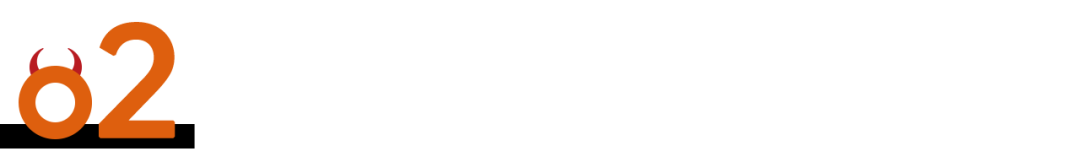
投资不是量子物理,越简单越好
投资这事看上去不难。事实上,它真的不难。很多人喜欢把它搞得复杂,其实完全没必要。
你不需要高深数学知识,甚至连中级数学也用不上,也不需要对技术有多深的洞见。
最终你需要理解的,不过是类似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人们爱喝可口可乐?未来会不会继续喝?这家公司过去一百年发生了什么?未来一百个月大概会怎样?就这么简单。
你不需要读商学院,也能成为优秀的投资者。
如果你身处一个轻松的行业,你看上去就是天才;但如果你身处一个困难的行业,你看起来就像个笨蛋。
我用了二十三、四年才真正明白这个道理,然后我就退出纺织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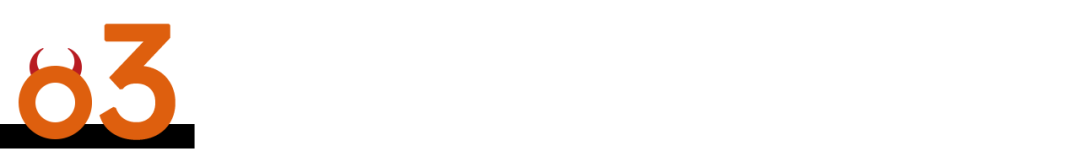
想赚大钱?专心“桶里捞鱼”
美国的管理者里,恐怕有99%的人都以为:我在一件事上很厉害,那我做其他事也一定行。
他们就像雨天在池塘里的鸭子,水面升高,他们也跟着往上浮。结果他们误以为,是自己在上升。但当他们走到没下雨的地方,就只能原地瘫坐,什么事也干不成。
然后,他们通常会炒掉副手,或者请个咨询公司。很少有人能明白,问题的根源是:他们已经走出了自己的能力圈。
我们公司以前有一位女士B夫人(Mrs. Blumkin),95岁的时候还在帮我们打理生意。今年她离开我们,现在96岁了,又自己干起生意来,直接跟我们竞争,而且一点不手软。她天天开着一辆高尔夫球车在店里转,从早干到晚,一周七天,非常强悍。
她在一件事情上极其出色。她从俄罗斯移民,落地美国西雅图时,脖子上挂着名字牌,一句英文都不会。现在在美国生活了77年了,英文还是说得磕磕绊绊。以前她打广告推销商品,听她说话你可能都需要加字幕,但她就是有那股劲儿。
她52年前用500美元创立了内布拉斯加家具城,如今每年税前利润达到1700万美元。她虽不识字,但能看懂数字。她不知道什么是“应计制”,会计知识基本为零。
但你只要告诉她这个房间的尺寸,哪怕不是规则形状,她马上就能估出这里需要多少平方码的地毯。然后乘上单价$7.98,再加上销售税,还给你打个折,而且算得一点不差。
她当然很聪明,但更难得的是,她非常清楚自己的能力圈。
你要卖她2300张小边桌,她一分钟就知道自己能付多少钱、多快能出货、利润是多少——然后她就会买。
她还会挑你最狼狈的时候出手,比如奥马哈下暴风雪,你急着赶飞机、不能误机的时候……她会压价压得非常狠。
她知道她能做什么,也知道自己要付出什么样的价格,而且从不会看错。不管是房地产还是信用调查,她都不会错。
但只要超出她的能力圈一寸,比如谈股票,她连10美分都不会投进去。她知道自己不懂,也非常清楚哪里是那条界线。
她可以凭眼睛判断一栋价值500万美元的楼,拍板买下,现金支付。但绝不碰任何她不了解的生意。
这才是真正聪明的人。这也是为什么她能把所有对手都打得落花流水。她白手起家,如今把奥马哈的大多数竞争者都挤出市场。
当年他们因为所谓的“公平交易违规”告她上法庭,四次之多,而她每次都自我辩护。
她走进法庭对法官说:“所有人都7美元一码卖这个地毯。我的成本只有3美元。我卖4美元也能赚钱。你就告诉我,你希望我从顾客身上多赚多少钱。如果你想让我多赚98分,我就卖4.98。如果你想让我多赚1.98美元,我就卖5.98。”
结果那位法官当场买了1400美元的地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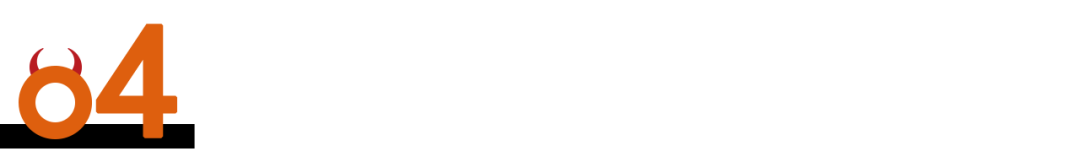
“彼得原理”的现实版,后面加了好几个零
真正能清楚划定自己能力圈的人,非常非常少。你去看看美国那些大公司的CEO,大多数都不知道自己的能力圈在哪,这就是他们老是做蠢收购的原因。
他们能一路爬到公司顶层,是因为他们是优秀的销售、优秀的运营者,或者其他什么方面表现出色。
但突然有一天,他们得经营一家几十亿美元的大企业,他们的工作变成了配置资本、收购公司。而他们这一辈子从来没买过一家公司,他们根本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于是他们通常会干两件事之一:要么组建一个内部部门,雇一帮人整天告诉他该干什么。
当然,这帮人也很清楚,如果他们没事可做,他们就没工作了,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们会忙成什么样;要么就是去找投行,而投行的收费方式是“做一单赚一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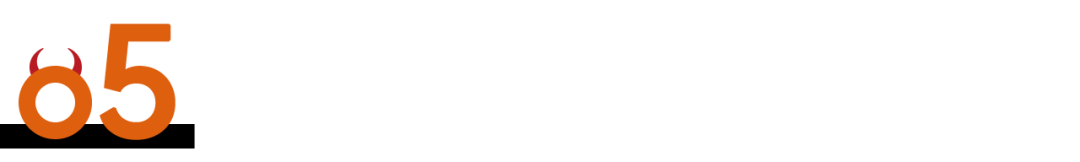
我不会的事情多了去了,那又怎么样?
我们从不碰自己不理解的生意。我们可能会判断错,但我们绝不会因为某家咨询公司,比如亚瑟·迪安·李特尔、博斯咨询、麦肯锡来告诉我们某家公司多么了不起,就去买它。
如果我们自己都不够懂,那我们根本不会参与。就这么简单。
我们从来不参考别人意见,永远只是查理和我俩人自己判断。这种方式有点危险,因为我们俩的脑子运转方式实在太像了。
但我们非常乐意放过世界上90%我们无法评估的东西。那又怎样?我也没法去打职业橄榄球。这个世界上我不会的东西多了去。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的能力圈并没有扩大多少。所以我们愿意等。等一年也行,等五年也没问题。
归根结底,查理和我能理解的生意始终只是少数几个。纽约证券交易所大约有1700到1800家公司,我们大多数都看不懂。
就算我花一年时间研究IBM或通用汽车,我可能能了解一些表面信息,但仍然不足以让我做出一个真正明智的投资决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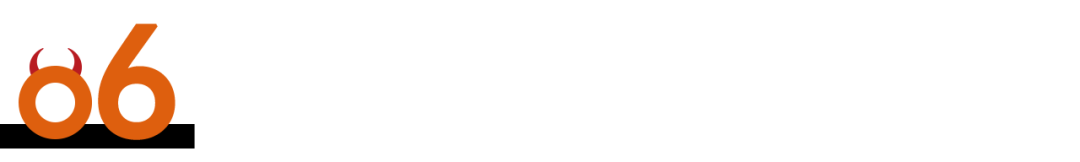
画出你的能力圈,然后待在里面
如果我们自己都不理解一个生意,就不会投资。我连什么是个人电脑都不知道,也搞不清谁家电脑最好。就算你告诉我现在谁最好,我也没法判断三年后谁会赢。
但我知道三年后美国销量最高的巧克力棒是谁,你也知道。你可能也知道哪款电脑能称王三年,但无论你怎么劝我,我对电脑的确定性永远不会像对巧克力棒那样高。
关键是要画出自己的能力圈,如果有疑问,那就给它加个“安全边际”,尽量待在圈子里。
看看汽车行业吧。如果你把1970、1975、1980、1985年全球五大汽车公司CEO都抓来、给他们打上“吐真剂”(巴比妥),问他们:未来五年哪家公司会是第一?——甚至未来两三年,他们都答不出。没人知道。
有些事情你就是不可能完全了解,也就没法靠这些判断去赚钱。我们宁可等一个确定的机会。虽然没有百分之百的确定,但偶尔市场会把机会摆在你面前,让你一看就懂。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规模太大了。要是只有1000万、1亿美元的资金,能遇到的好机会就多得多。但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耐心等。
我在商学院讲课时总说:如果每个学生毕业时能拿到一张“20次打孔卡”,每做一个投资决策就打掉一个孔,一生只能做20次,那他们一定能赚很多钱,因为每次决定都会慎之又慎。
但现在股市每天开着,你可以随时买AT&T、通用汽车、美国钢铁,买多、做空、进出任意组合。因为机会太多,人们就觉得“既然能做点什么,那我就应该做点什么。”
我们不会那样干。我们只等那些一看就“很明显”的机会。
问题是华尔街的机制完全相反,一直在喊:“做点什么!做点什么!”因为交易活跃才是它的奶和蜜。
很多人只是因为屏幕上不断跳动的小数字,就觉得自己必须干点什么。
我觉得吧,如果股市能时不时关上几天,人们反而会过得更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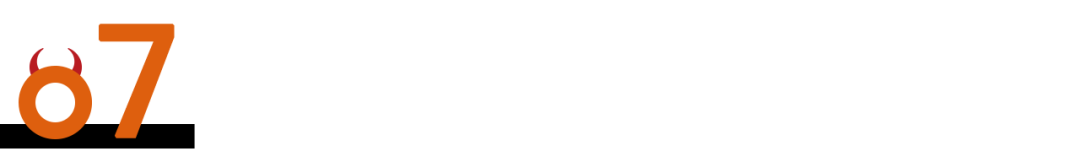
我们更愿意把开疆扩土的事儿留给别人干
我们比很多管理者多一个显著优势:我们愿意只买下企业的一部分。一般的职业经理人只想买下整个公司,或者是自己能管理的生意。所以他只能买别人正好要卖的,或者是能发起敌意收购的标的。
我们现在持有可口可乐公司7%的股份。也就是说,按全球软饮市场来看,伯克希尔相当于占了3%的市场份额。没人会这么想问题,但事实就是如此,我们现在是全球市占第三高的“软饮公司”了。因为可口可乐的市占率是45%,而我们持有其中的7%。”
绝大多数经理人不会去买可口可乐,即使它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生意,因为这对他个人没什么“好处”。他不会因此多几个下属,办公室不会更大,表面上看一点成就感也没有,不够男子汉气概。所以他就不会去买这个生意,哪怕他心里知道这是最好的。
于是他就开始去看市面上正在出售的,或者是他能发起敌意收购的标的。而敌意收购是什么?本质上是一场拍卖,全球所有买家都在和你竞价。在那种情况下,他最后只能出到最高价,才能拿下那家公司。
这样一来,他既不会买得便宜,也买不到最好的生意。而我们可以直接买世界上最优秀的公司,只是买不下全部股权罢了。对我来说,这一点都不重要。
我宁可让别人去干活。想想吧,有哪个男人好意思让一个95岁的老太太替自己每周干7天?
我非常乐意让罗伯托·戈伊苏埃塔(Roberto Goizueta)和唐·基欧(Don Keough)替我们到全世界宣传可口可乐。他们每天要卖出6亿瓶八盎司的软饮料。我们持股7%,那就等于每天有4200万瓶是替我们卖的。”
如果这些饮料分布在全球各地,那就意味着,当我在睡觉时,有1400万人在喝我们家的产品。
而且这类产品基本上没有可替代品。在美国,百事和可口可乐有时是可以互换的,搞不好还要打价格战。但在世界其他地方,可口可乐没有对手。它在155个国家都是销量第一,而且市占率每年还在增长。消费者不是在找最便宜的饮料,现实不是那样的。
我们可以持有这家公司的一部分。我们买不下全部,但我宁愿用合理价格买一部分优秀的生意,也不愿在竞争激烈的拍卖中,用高价买下一个当下能买到的“完整“但平庸的公司。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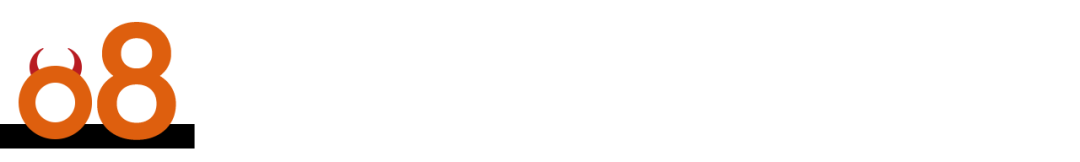
伯克希尔偏好的投资方式
在美国,真正愿意用自己钱去投资企业的人很少。大多数人都是拿别人的钱去投。
但在伯克希尔,查理和我都是拿自己相当大的一部分身家来投资的。放眼美国,很难找到第二家公司,它的管理者愿意用这种比例的自有资金去买其他企业的股份,而且长期持有,不去谋求控制权。
他们等于多了一个真正“把大量自己的钱压进去”的股东,会真正关心公司的长期成功,而且不会被过去的决策束缚,也不会被原有的思维圈子限制住。
这本身可能很有价值。说得直接一点,如果用对了我们,他们就能获得我和查理之间那种互相对话的价值。
查理不是天天管事儿,但他始终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评审人”。他自己把钱放在伯克希尔里(不过对他的判断毫无影响),而他会毫不客气地告诉我对某个点子的真实看法。大多数点子他都不喜欢。
我们确实能为公司带来价值,对某些公司尤其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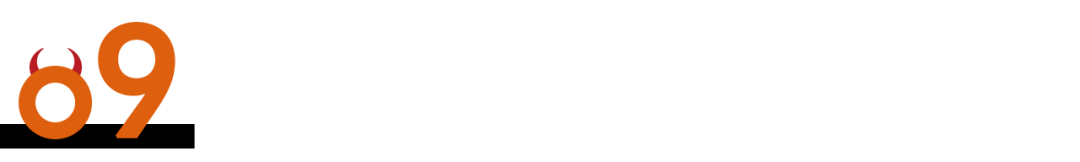
我们喜欢的交易方式,对普通股东最有利
我们手里的这些优先股,税前收益大概9%,税后差不多不到8%。但如果伯克希尔只能做到税后8%的资本回报,那说明我们做得不怎么样。所以,这些交易必须存在一种可能,即公司的普通股未来会涨。
我们确实有收益率的优势,也有大约十年左右的强制赎回条款,这意味着到时候我们至少能按成本价退出。
但除此之外,我们其实什么控制权都没有。这些协议都有“持股上限”条款,阻止我们继续买到控股地位。我们不控制这些公司,也不想控制。
如果普通股未来不涨,我们至少还能赚到一些额外收益;如果普通股涨了,我们赚不到像普通股股东那样多,毕竟可转优先股永远不可能比普通股赚得多。如果我们在普通股上赚钱,普通股股东赚得会更多。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我自己持有某家公司1%的股份,而查理没有跟我一起投资,我会很希望他去持有我们这种优先股头寸。因为那意味着他会拿出很多自己的钱,而且会拥有不少投票权。
如果我是普通股股东,而查理持有优先股,那上涨的时候我赚得更多;下跌的时候,他的保护更强,而且强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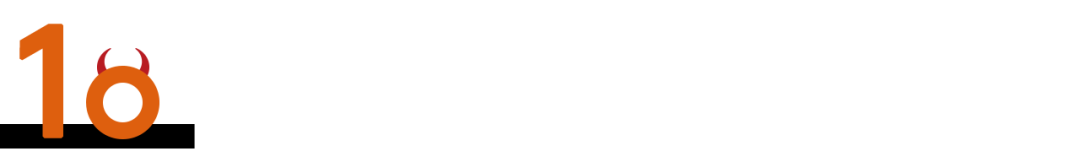
时代真的变了
我想分享一个小插曲,是关于1957年大都会公司(Capital Cities)首次上市时的故事。虽然我没有百分之百确认,但据我记忆,这可能是大都会唯一一次公开募股。
他们最早确实从洛厄尔·托马斯(Lowell Thomas)和其他几位个人那里融过一些钱,后来合并ABC时也从我们这边拿过一点,但那次IPO是他们首次真正向公众融资。”
最有趣的是,这笔29.9万美元的公开发行,居然用了两家承销商来促成:一家叫Harold C. Shore,听着像个街坊名字;另一家是来自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的First Securities。更不可思议的是,两家公司总共只拿了6500美元的承销费。
所以啊,每天大家都在骂华尔街贪婪的投行,可至少在1957年大都会上市时,投行还没那么狠。
回顾1957年大都会上市时的对比数据:当时CBS的年营收已经接近4亿美元,而大都会连100万美元都不到。CBS银行账户里有4600万美元,大都会只有10万美元。
CBS拥有全国电视网和一堆电视台,而大都会的第一家电视台在奥尔巴尼,原本是供修女养老的地方。那个祷告室被改成了演播室。
这个地方破得厉害,董事会有一次逼着CEO汤姆·墨菲(Tom Murphy)去刷漆。他也听话,下一次会议前真的刷了漆,但只刷了面向马路的那一面(笑)。
他们只有一辆新闻车,却贴着“第六号车”的标志,感觉就像在演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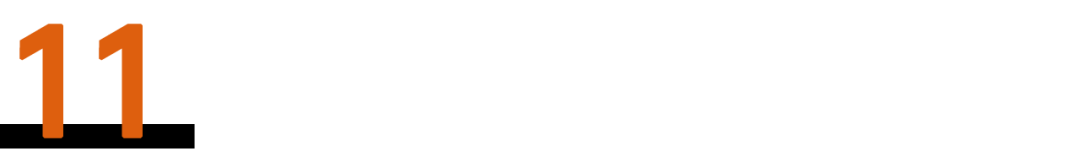
关于电视、CBS和汤姆·墨菲
电视注定是个好生意。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三条“电子高速公路”,也就是三大电视网。任何想要向全体美国公众传递信息的人,基本就只能通过这三条渠道。
那是电视行业的黄金时代。现在不再那么美好了,但当年真的棒极了。
说到底,电视就是个分发渠道。分发渠道的价值,取决于有几个管道。如果只有一根管子,你能赚大钱;如果有十根、二十根,你就很难赚钱。报纸也是一样的逻辑。
你看CBS和大都会当年都是在同一个好赛道上,一个拥有全部资源,一个几乎什么都没有。一个像坐着“伊丽莎白女王二号”从伦敦启航;另一个像划着一艘漏水的小船。但几年后,两者都抵达了纽约。而划小船的人还先到一步,且载货更多。
你在全世界也很难找到比汤姆·墨菲更好的管理者了。他是顶尖中的顶尖。他在一个优秀行业里,创造了巨大的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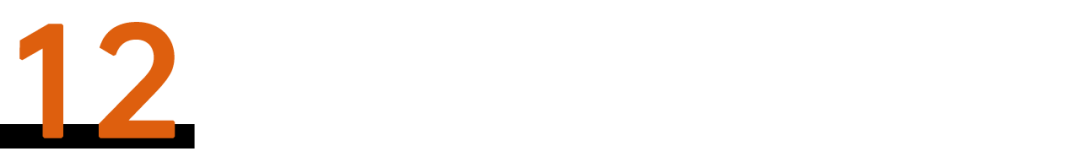
价格竞争的极限在哪里?
我们在1972年买下喜诗糖果(See's Candy)的时候,它的售价是每磅2美元。今天已经卖到8美元一磅。”
你能想象情人节回家对太太说:“亲爱的,这是给你买的巧克力,我找了最低价,才2.85美元一磅,在小巷子里买的。吃之前你最好擦擦。”这样你还想保住婚姻吗?
在礼品场景下,几乎没有价格竞争者能打入这个市场。
你愿意走进药店,花便宜几分钱去买一块包装简单、只写着巧克力棒的东西吗?不会的。你想要买的是好时(Hershey)这样的品牌。如果没卖好时,我宁愿走到街对面。
分销不是问题。我完全可以推出“巴菲特牌巧克力棒”,但没人会买。
好时的市场壁垒根本打不破。你去看现在最畅销的几款糖果,再对比20年前,几乎一模一样。
当然,各家都在努力挑战彼此。玛氏(Mars)一直在想办法击败好时,好时也在研究如何对付玛氏。吉百利(Cadbury)甚至远渡重洋来到美国,试图撼动这个市场。不是没人尝试,只是都没法撼动这个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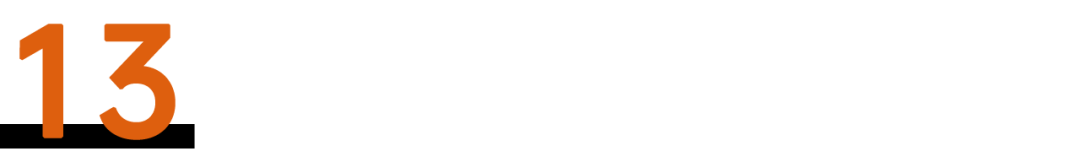
最好的生意,是不需要投入太多资金
大约一年半前,《每日赛马表》、《电视指南》和《十七岁》杂志这三个品牌被以30亿美元的价格卖出。它们几乎没有什么有形资产。
但它们各自拥有城堡和护城河:其中《赛马表》是一座小城堡,护城河很宽;《电视指南》是一座大城堡,护城河更宽。
企业的价值,取决于这座城堡的规模,以及护城河的宽度和深度。这跟科技无关,跟超级碗也没关系。
有趣的是,这其实有点反直觉:如果一家公司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能赚到同样的钱,那资产越少,反而越值钱。你在会计课上是学不到这个的。
真正让人梦寐以求的生意,是那种根本不需要往里砸钱的生意——因为它已经被证明:即使你花再多钱,也无法在这个行业里争到一席之地。这样的生意才叫伟大。
在一个极其出色的生意里,你几乎不需要投入任何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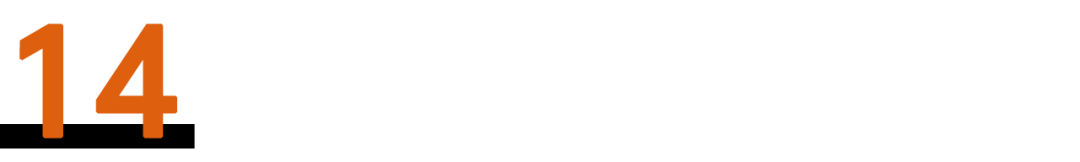
风险套利:核心是判断概率与结果
风险套利这件事我已经做了40年,我的老师本杰明·格雷厄姆也做了30年。只要世界上存在两个市场,套利就存在。
比如以前奥马哈和芝加哥都有小麦市场,价格出现偏差时就会有套利。这种就是纯粹的套利,如今在货币、商品领域仍然存在。
风险套利则是针对已经公布的企业事件进行的套利。我今天来这之前,还接到公司打来的几个电话,都是在处理我们手上正在做的套利交易,它们都涉及已经公开宣布的事件。我的工作,就是判断这些事件真正发生的概率,以及潜在的盈亏比例。
比如说,一项交易有90%的成功概率,预期上涨空间是3点;10%的失败概率,可能亏损9点。那么,这笔交易的期望收益是90%×3=$2.70,10%×9=$0.90,净期望收益就是$1.80。然后我们再考虑持有时间。
数学不复杂,关键在于你怎么判断概率,以及你对上涨和下跌空间的把握。
这是一种投资行为,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研究未来十年资产价值”那种投资,而是基于短期事件公告,对当前价格进行评估。
我们只在看准的情况下参与。一年中,能符合我们标准的也就十几宗。早年我资金不多的时候,一年可能能看一百宗。
(编辑注:此后伯克希尔曾提交13-D文件,披露持有Rorer Group(一家医药公司,当时正面临被以换股方式收购,且消息已经公布)的股份,这被认为是一笔典型套利交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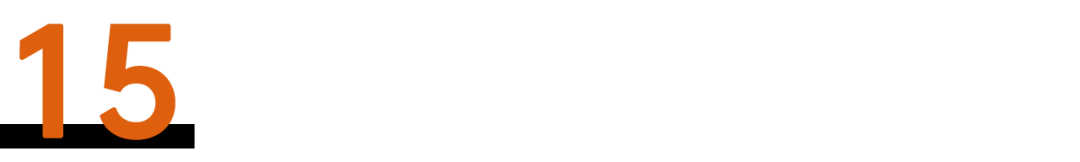
波仙珠宝就像内布拉斯加大学橄榄球队
我太太苏珊能给你解释为什么波仙珠宝(Borsheim's)是我们最棒的一笔投资。
它几乎不需要我操心。我花点时间纯粹是因为我喜欢,不是它真的需要我。就像内布拉斯加橄榄球队周六比赛时需要我一样——完全不需要。
它不会分散我对其他事情的注意力,也不会占用我给可口可乐的时间或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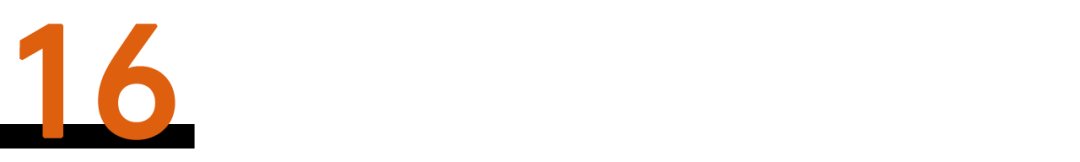
规模和关注度是投资的敌人
当年我们投资可口可乐,最大的限制是:在股价还对我们有吸引力的时候,我们到底能买进去多少钱。
我们一般会尽量把买入时机安排得更好,在需要公开披露前尽可能多地建仓。
我们买到接近目标持股了。要是能一直按之前的价格买,我会买更多,但也不会夸张到买到特别大。
我们从6月开始买,到次年3月结束,整整花了8、9个月才买进7%的股份。而在同一时间里,可口可乐公司本身也在回购股票。
所以那段时间内,公司和我们加起来,相当于买了公司12%的股份。想想都觉得惊人。
体量大了,加上市场关注,确实让事情变难了。但好在这对我个人生活没什么影响。
不过确实“搭便车”的现象越来越多。但比起市场关注,规模才是更大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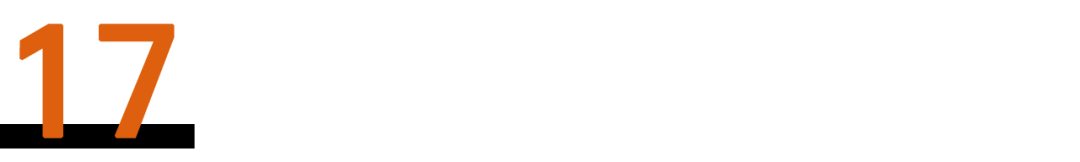
你永远无法比你最蠢的竞争对手更聪明
伯克希尔公司在公务机上的开支按年化算翻了一倍,这不是飞机升值的原因,而是我的品味变了。我们花85万美元买的那架,后来卖了100万美元——那是市场行情。而现在这架,只是反映了我变得更愿意纵容自己了。
航空业是个糟糕透顶的行业。如果你在25年前问:是航空运输业会增长得更快,还是爱荷华州Council Bluffs那些小城市的几家报纸会增长得更快?你一定会说航空业。
结果航空业的确增长得更快,单位销量涨了很多倍,但从盈利的角度看,它几乎是你能想象的最烂的生意。
TWA是美国最老的航空公司之一,过去40年没赚过钱。泛美、东方航空也没赚过钱。这不是因为他们把钱分掉了,而是根本没赚到钱,尽管每年载客量都在增加。
航空业是个非常艰难的行业,资本密集、劳动力密集、产品还高度同质化。你很难想出比这更糟糕的行业描述了。你做的就是不停烧钱,没有喘息的机会。
而且竞争一定是价格战。只要有人开始送常旅客积分,第二天就会有十家跟上;如果有人送双倍积分,又会有十家跟进。在这种行业里,你必须跟着竞争对手的动作——无论他有多蠢。
这就像过去街角的四家加油站,有一家降价,其他三家五分钟内就得跟着降。在商品化的行业里,你永远无法比你最愚蠢的竞争对手更聪明。
这点我很早在商学院就学到了,那是他们少有教对的事情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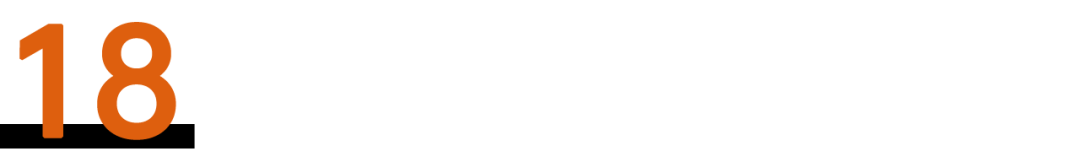
我们可不喜欢瞎折腾
当我真的想买点什么的时候,我的正常反应就是,恨不得把自己的全部身家都压进去。我们向来就是这么想的。只有这样,你才能赚到真正的大钱。能过这种筛子的点子,本来就不多。
如果你把我们过去四十年里“大点子”和“小点子”做个对比,光看组合占比和最终效果,那差别简直天壤之别——大点子远远更赚钱。
这也是为什么我常说:你的人生投资卡上最好只有20次打孔机会。
我经常被问到,“这个机会要不要小赌一把?那个要不要试一下?”我从来不回答。答案永远是:别干这种事。
只做那些你愿意投很多钱进去的事。如果你不愿意投大钱,那它就不是个好主意,那就别做了——就这么简单!
除了某些特定的套利情况之外,我从不买任何我不愿意拿自己10%身家押注的东西。如果我不愿意押进去,那它就根本不值得我花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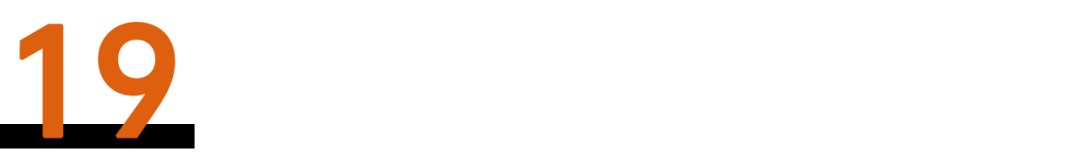
为什么不愿意用80美分买1美元?原因在这里
你可能会说:既然你愿意50美分买1美元,为什么不在80美分的时候也买?
因为你知道,未来你大概率还能在5毛钱的时候买到,无论是同样的1美元,还是别的资产。
你会给自己设定一个非常宽的安全边际——尤其是在你准备投入新资金的时候。买入必须足够便宜才行;至于什么时候卖出,就不是按照这套逻辑判断了。其他还有一些原因,但这就是最核心的经济考量。
你不能因为某样东西值1美元,而你能用5毛钱买到,就想当然地认为:当价格涨到5毛1分时,你必须赶紧卖掉,然后去买另一只同样是5毛钱的便宜货。投资不是那么精细的游戏——除非你只是在比较不同期限、不同利率的国债。
资产都会在一个宽区间里波动,而只要你知道自己买入的是低于价值的东西,你又认为价值会继续上升,那你依然会感到很舒服。只是这个价格,可能已经没有便宜到让你愿意掏“新钱”去买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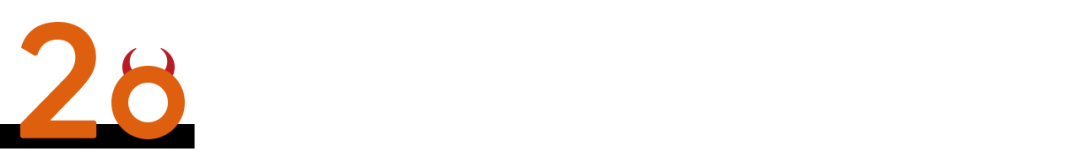
便宜的更危险?胡扯
查理和我都不认为现代投资组合理论(MPT)有任何道理,我们觉得那一套逻辑基本都是瞎扯。我们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在承担风险。可MPT却把“股价波动”当成风险的核心。
1974年我们买下《华盛顿邮报公司》时,给出的估值是8000万美元。但就在同一个晚上,如果你去找买家,它立刻能卖到4亿美元,而且真会有五个买家当场愿意拿现金买下。
那时候如果你问100个分析师这家公司值多少钱,没有一个人会否认它值4亿。
但他们卖的理由只有一个:股票下周不会涨、下个月也不会涨,所以干脆卖了事。
而我们在一两个月里,以8000万的估值买下了公司接近10%的股份。
按照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和beta的逻辑,我们如果用4000万买股票,反而比用8000万买更“高风险”。虽然它明明值4亿。看到这,我就直接弃疗了。
当然,有些情况下风险和回报确实有关联。可如果你买的东西足够便宜,那么就算它继续下跌,那反而是更安全的。
你用8000万买下《华盛顿邮报》比用1.2亿买要安全;用4000万买,更是安全得多。
当然,这前提是——你真的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而现代投资理论的默认前提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所以它才会告诉你应该怎么分散投资、怎么算beta。
我一直很好奇,他们怎么能把整门课讲满。因为他们假设市场是有效的、一切都定价合理。那后面的课还能讲什么?我真是想不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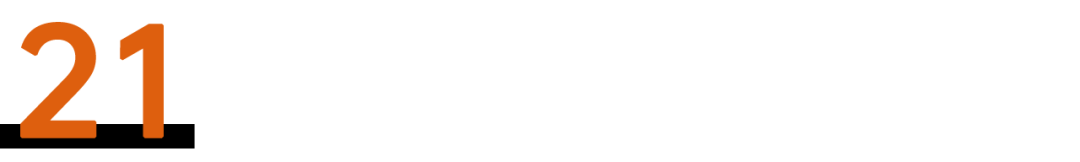
最糟糕的竞争,来自海外
一般来说,我不喜欢进入那种“全球竞争”的行业,原因跟我之前说的一样——我连国内竞争都不愿碰,更别提全球范围了。
而且全球竞争只会更难。为什么有些制造业要搬到台湾或其他国家?背后往往有长期的结构性优势。比如,人家那边律师可能更少。我们这儿一遇到诉讼,成本就飙升,做个小小的零件也变贵。
各种成本差异长远看都可能对我们不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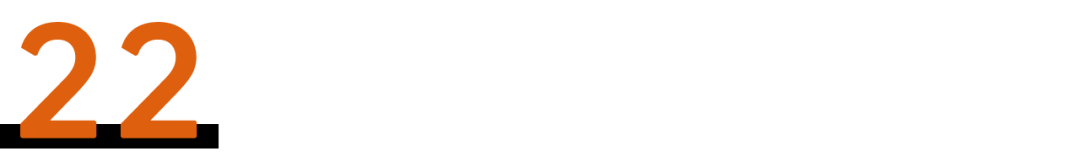
我有一个惨痛的提醒:海外风险有多现实
我个人更偏好在美国注册的企业。苏珊和我各自还留着一股我在1955年买的股票。当时看上去无比安全,是一支很棒的股票。
结果就一个问题:公司的资产在哈瓦那,被卡斯特罗没收了。产权拿不回来了。那些房产现在就在那里,我们也向政府报了巨额索赔,但永远都不可能值钱了。
我把这股股票留着,就是提醒自己:在别的国家,规则可能一夜之间就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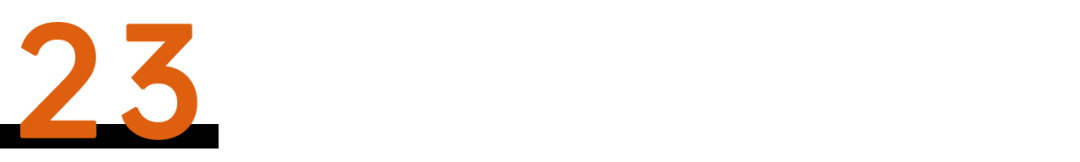
我们从不搞敌意收购
我们只买那些欢迎我们进入的公司。我经常在买入前就告诉公司管理层:我只会买到你们觉得舒服的程度。
比如当年我们买《华盛顿邮报》的股票,凯瑟琳·格雷厄姆(Kay Graham)在我们持股快到9%时感到不安,我就说:“好,那我们一股都不再买了。”就这么简单。
我希望管理层感到安心。否则他们可能会因为紧张,做出很多愚蠢的事,比如以过低价格增发股份。我希望他们能做聪明的决定。
通常我们会买到那个“舒适线”附近,我也都会提前跟他们沟通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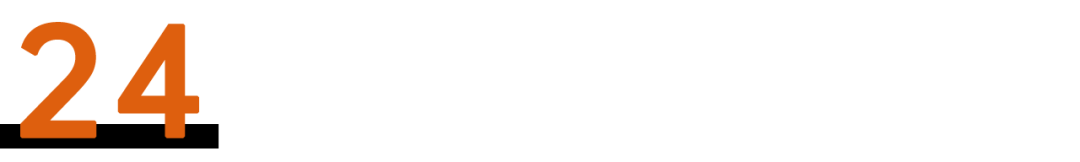
伯克希尔的谈判风格
我们谈判的方式和别人完全不同。
当年买下喜诗糖果,我只在那儿待了一个小时。我们买的所有生意基本都是一个电话谈成的。
买波仙珠宝的时候,我到艾克·弗里德曼(Ike Friedman)家坐了半个小时,他给我看了一些没审计过、用铅笔随手写在纸上的数据,就这么定了。
如果一笔交易需要带上一堆律师和会计师,那它肯定不是什么好买卖。我们从不和人反复拉扯谈条件,这不是我们的风格。
如果一开始他们就想把谈判搞得又长又复杂,我就不想跟这种人打交道。这迟早会把我的生活搞得一团糟,所以我们干脆直接走人。
风险提示: 投资涉及风险,证券价格可升亦可跌,更可变得毫无价值。投资未必一定能够赚取利润,反而可能会招致损失。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将来的表现。在作出任何投资决定之前,投资者须评估本身的财政状况、投资目标、经验、承受风险的能力及了解有关产品之性质及风险。个别投资产品的性质及风险详情,请细阅相关销售文件,以了解更多资料。倘有任何疑问,应征询独立的专业意见。
推荐文章
港股周报 | 中国大模型“春节档”打响!智谱周涨超138%;巨亏超230亿!美团周内重挫超10%
一周财经日历 | 港美股迎“春节+总统日”双假期!万亿零售巨头沃尔玛将发财报
一周IPO | 赚钱效应持续火热!年内24只上市新股“0”破发;“图模融合第一股”海致科技首日飙涨逾242%
从软件到房地产,美国多板块陷入AI恐慌抛售潮
Meta计划为智能眼镜添加人脸识别技术
危机四伏,市场却似乎毫不在意
美股机会日报 | 降息预期升温!美国1月CPI年率创去年5月来新低;净利、指引双超预期!应用材料盘前涨超10%
财报前瞻 | 英伟达Q4财报放榜在即!高盛、瑞银预计将大超预期,两大关键催化将带来意外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