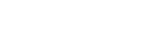热门资讯> 正文
52种小说|一个草包如何在一夜之间被包装成文坛明星?
2025-02-14 15:02
- 维捷(VJET) 0
本文已经得到“后浪”授权,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
不管你觉得《羊奶煮羊羔》的开头读起来怎样,只要翻过几页,你就会被波利亚科夫机关枪一样的语言节奏席卷。这些句子它看上去无辜又简洁,几乎不带情感修饰,语气像苏联笑话一样克制,内容也像,一个长篇版本。享受波利亚科夫的语言密度本身吧,讽刺是他的堡垒,也是他的武器。
我们选取了《等待维捷克》一章,发布如下:
我回到家中,维捷克还没有回来。我对着瓶口喝了点“败德汤”,就坐下来写少先队的致敬信。致敬信是我心爱的话题!我写了多少致敬信呀,简直数不胜数!这不是工作,而是享受。有些专家认为,在全世界的文学中,总共不过有十二三个情节,其余都是它们的变体。如果要说少先队的致敬信嘛,它只有开创于 30 年代的一种类型。其余的都是它的变型。
我取出先前作品中的一篇(我把自己作品的复印件装订成了一个专用卷宗),便开始改写。其做法是,比如:
我们头顶上飘扬着胜利的红旗, 就像是誓言,传来了欢呼: 我们幸福地与您生活在同一时代,亲爱的列昂尼德·伊里奇!
顺便说一句,这是我最好的致敬信之一。据说,勉强蹀躞行走的勃列日涅夫感动得甚至落了泪。结果,我不仅收到了允诺的酬金, 还免费得到一张去保加利亚金色沙滩的疗养证。在那里,我和斯涅然娜爱得死去活来。她是来自大特尔诺沃的姑娘,长得像甘草冰糖一样,黝黑,香甜。我们游得离海岸远远的,在无边无际的海上互相爱抚,被幸福与苦咸的海水呛得喘不过气来。不过,只有和安卡在一起才那么舒服......斯涅然娜深深地爱上了我。她再三追问,难道发生了这一切之后,我们还能分手吗。我反反复复地点头。与所有其他民族不同,在保加利亚,这表示:“不,永远不!”她一直问, 我爱她是否胜过生命,我则否定地摇头,在保加利亚,这正相反,表示:“是的。”人们说,与女人说话最好用法语。不对。只能用保加利亚语!
不过,还是回过头来说致敬信吧。当然,写完上述那封热情洋溢的致敬信之后,国家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内容也迫切需要做原则性的修正,需要反映祖国新的客观现实。我想了一番,改写成如下方案:
我们头顶上飘扬着胜利的红旗,像是誓言,传来了欢呼: 我们幸福地与您生活在同一时代,亲爱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当然,这算不上什么名作,但如果朗诵水平高,还是说得过去的。工作进行得愉快而顺利。可是,当贺诗全部写好,并已交给订货人以后,困难来了。其中就包括这四行诗。虽然当时我已经到了谢米尤尔金斯克,通过谢尔盖·列昂尼多维奇,意识形态专家茹拉夫连科还是找到了我。他正好管这个致敬信。
“这不行!”他努力用吼叫压过长途电话里的沙沙声,“您忽视了新的社会生活现实。而且,重音怎么能落到‘维奇’上去呢?这给人以过分机灵的印象。必须重写!”
在那个时候,现实确实变了,而且其中还有我的一份功劳。刮起了阵阵清新的风,改革已经宣布开始。只得再做努力:
红旗在强劲的春风中漫卷, 改革的呼声亲切地响在耳畔,与你生活在同一时代无限幸福,亲爱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新贺词我托埃奇格利德耶夫带到莫斯科,他正好被召去参加某 个会议。怒不可遏的茹拉夫连科隔一天又打来了电话:
“您怎么就听不明白呢!新思维在哪儿?而且,总的来说,怎么能直呼总书记的名字呢。立即重写!”
“您知道吗,我绝对是故意这样写的 ......” “那对您来说更糟糕!” “请听我把话说完!国家的新领导人与早先的领导人区别在哪里?或者您以为,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与列昂尼德·伊里奇或是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没有任何区别?”
“不,我不这样认为!”茹拉夫连科赶忙申明,“他是新型领导者。”
“既然他是新型领导者,我们就应当以新的方式对待他!您同意吗?”
“同意。”
“如果我们以新的方式对待他,称他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这就是强调他与生俱来的民主精神!”
“您这样认为吗?”沉默良久之后,茹拉夫连科问道。
“您自己想一想啊,美国人不是称自己的总统为罗纳德·威尔逊·里根吗?”
“有道理。我要想一想。” 他想了一想,决定保留原来的方案,但要求我补写关于新思维的一段。我补写了:辫子上系着洁白蝴蝶结的可爱姑娘们,在充溢大厅的笑声中,从讲台上取走了“旧思维”— 用混凝纸浆做成的大脑模型,模型上涂着各种油彩,皱巴巴的十分难看。她们又从后台拿来另一些模型,很大,很漂亮,充满了创造性思维的脑汁...... 戈尔巴乔夫出席了会议,少先队员的致敬信使他笑逐颜开。他刚在伦敦会见过撒切尔夫人,铁娘子就直接称他为麦克尔。总书记很喜欢:在交给他掌管的国家里,甚至连孩子们都直接称呼他为米哈伊尔。着手改革之前,他曾忧心忡忡,自己能否撼动这个沉睡的愚昧的庞然大物呢?不料,从这个大国的年轻基础中,迅速得到了如此朝气蓬勃的反应!我先提前交代一下,因为敏锐感受到了社会生活的变化,茹拉夫连科得到大力提升。不过,他也确实是个敏感的人: 他是最早投靠叶利钦的人之一,下一次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是以全新的身份— 俄罗斯第一位候选总统竞选班子的负责人。根据他的订单,我设计了一幅宣传画,您当然还记得它!请想象一下: 在巨幅有光纸上印有三位女神的彩色画像(不过摆出的是选美大赛 优胜者的姿势),而一旁则是沉思中的帕里斯,他很像一位普通选民。但主要的是我的两行诗:
如果我是帕里斯,
我一定选择鲍里斯!
这幅宣传画曾被所有民主派报刊翻印。我被选入支持叶利钦的 谢米尤尔金斯克选民委员会,他们还给我发了一百美元的奖金,这是我在与外币无缘的生活中靠诚实劳动挣得的第一份外币!等待我的完全有可能是灿烂辉煌的仕途,茹拉夫连科甚至打听过我何时才能回到莫斯科。然而,一些不幸的事件拖住了我,而且,我不小心,还几乎免费为自由民主党库梅尔分部撰写了一首宣传诗:
要想时时处处都有秩序,
那就大胆支持日里诺夫斯基!
我在政治上欠缺原则性为众人所知,这毁了一切。天哪,我明白得太晚了:无原则性精神必须是彻底的,大气豪迈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够指望在政治上飞黄腾达。茹拉夫连科就是这样做的。顺便说一下,现在他已经离开叶利钦,组建了自己的民主爱国党。我估计,茹拉夫连科自己将竞选总统。在飞往卡塔尼亚之前,应他的请求,我为未来竞选用的宣传画写了这样的题词:
有一个思想必须时时牢记: 从我们民主爱国党的立场上看,生命与奋斗的根本意义, 就在于扫除群众的慵懒,让他们挺直自己的腰杆,让俄罗斯 — 重新崛起! 然而钱暂时还没有得到 ......
是的,毁掉戈尔巴乔夫的,是他对敏感、机灵而又善变的战友们的宠爱。而断送叶利钦前程的,则是他对精通多种外语的战友们病态的爱!对一个青年时期未得到良好教育的人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弱点......在这里我忍不住要回忆一下发生在“房产商”身上的一件事。他早年毕业于乡村中学,由于交通不便,远离文化中心,学校里几乎不教外语,只是总务主任给上过几堂课。战争行将结束时,他被德国人赶往德国做劳工,途中被我们的军队夺下来,遣返回了家。暴富之后的“房产商”长时间不能结婚,因为他一定要找一位精通一门欧洲语言的姑娘,最好是英语。他甚至花高价聘请了媒婆,她还真给他找到了。姑娘长相一般,算不上清纯女子,但毕业于特种学校,在国外进修过,用莎士比亚的语言讲起话来像小鸟一样动听。最初的一段时间“房产商”相当幸福。后来他开始发现自己妻子有许多不正常的地方:有时候笑得不合时宜,有时候用酸奶皮煎荷包蛋......“房产商”决心查询一下,结果查明,她的确毕业于特种学校,但这个学校是莫斯科唯一的特殊学校,它采用独一 无二的有损于智力发展的教学方法给孩子们教外语。这个教学法收效神奇,尽管不能增添智力,却能保证学到完善的外语知识。这个教学法的发明人,就是这所学校的校长,他通过了论文答辩,并获得了国民经济成就展览馆金质奖章。“房产商”妻子的怪诞日甚一 日。这时盖达尔的改革刚好开始,她在电视里看见某位改革派部长, 便 立 即 鼓 掌 , 大 声 吹 嘘 道 :“ 我 跟 他 在 一 所 学 校 学 习 过 !”“ 房 产 商 ” 本想离婚,但不那么容易— 她已经怀孕了。刚开始他很苦恼,尤其为未来的婴儿担忧。可是后来他想道:既然这所特种学校的毕业生已经当上了部长,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现在他那个有些古怪的儿子年仅三岁,“房产商”已经为他交了预付款,在这所奇妙的特种学校里预订了一个位子!
维捷克很晚才回来。他乌云满面,简直都认不出他来了。“喂,她的回忆录写得怎么样?”我问。“你和你的老婆子都滚蛋!”
下面紧跟着便是一套套别出心裁的詈骂用语。这些话让一个人想出来当然会力不从心,它们只能诞生于祖国几代建设者在可怕的劳动组织条件下的共同努力之中。骂够以后,维捷克进了浴室,但马上又拿着一管洗浴香波出来了:
“你有没有更厉害点的?” “这是什么意思?” “嗯,就是有洗衣服的肥皂吗?” “没有。”
“洗衣粉呢?” “有,在浴盆下面。”
出于好奇与同情,我跟在他后面看。维捷克找出一盒尚未开封的荷花牌洗衣粉,撕开后,将之全部撒进了热水里。然后他脱光衣服,钻进了没脖子深的水中。
“要给你搓搓背吗?” “你滚!”
紧接着就是更加别出心裁的詈骂用语,它们与上面那些用语的区别大致就像英国作家马洛的《浮士德》与歌德的《浮士德》之间的区别。强大的与无限充实的俄罗斯人民啊!
日古托维奇这时候来了电话:“睡下了吗?”“正在劳动。” “听我说,也许,给阿诺尔德打个电话?让他再送些‘败德汤’来!” “很糟吗?”
“糟得没法再糟啦 ...... 打个电话吧,啊?” “那你就打吧!我现在就告诉你电话号码。” “不,你来打。在餐厅里的时候他生我的气了!” “他做得对!以后你就不会再嘲笑人了。你生在莫斯科并不是他的过错嘛 ......” “你打吧,”日古托维奇继续恳求道,“老婆已经到了极限!说不定,你那里还剩一点吧?” “好吧,我打电话。”我同意了。我看了看酒瓶子,还剩不足一茶杯。为了从粗制滥造平稳过渡到创作“首要”作品,这些显然 不够。
“咱们的维捷克在做什么呀?”受到鼓舞的斯塔斯问道。“为什么是‘咱们的’呢?”“噢,你的,你的。”
“在澡盆里,正在洗涤自己的罪孽。”
“我去了一趟文学家宫。大家正纷纷议论他。”日古托维奇忧郁地说。“明天还会有新情况!”
“什么情况?”
“你明天就知道了。你认识基皮亚特科娃吗?”“认识 ...... 她有时会来我们书店 ......” “那么,她下一次去时,你问问她关于阿卡申长篇小说的事 ...... 你怎么不吱声呀?”
“你要我说什么?”
“星期三读一读《文学周报》,那里有扎库松斯基关于我的维捷克的文章。”“噢,这还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荣誉。” “老母鸡吃米,一粒一粒地啄吧!”“你反正赢不了!” “赢得了!所以你快些读完自己的《百科全书》吧,我已经在书架上为它腾好地方啦。你在《百科全书》里又读到什么有趣的东西啦?”
“还是那些,”日古托维奇压低声音说,“俄罗斯的革命原来也是共济会搞的。克伦斯基是共济会会员。其他人也都是。列宁大概也是,不过那上面没写。总之我很惊讶:只要是稍微有点名气的历史人物,就是共济会会员 ......”
“也许,他们之所以是历史性的卓越人物,就是因为他们是共济会会员?”
“我考虑考虑 ......” “考虑吧!晚安!”
我挂上电话,感到非常满意。因为我刺痛了自负的日古托维奇。突然,我感觉到房间里有一股洗衣房里才有的刺鼻味道。原来是维捷克洗完澡出来了。
“共济会都是些什么人呀?”他问。
“怎么才能给你解释清楚呢,”我说,“三言两语说不明白。有许 多说法,写了几十本书......不过,如果一定要用三言两语来说,那么,这是个秘密团体 ......”
“它还算他妈的什么秘密的呢,要是写它的书就有几十本?这有点像我们工地上的一个秘密团体。三个小伙子把建筑材料从施工现场弄走,卖了。为了让我们别吭声,便每天给我们酒喝。不过给施工员的却是钱 ......”
“抓住他们啦?”“没有 ...... 至今还在偷!” “你看,”我点了点头,“你还为共济会的事感到惊讶。道理是一样的......维捷克,你不要生我的气!唉,通向光荣的路用臭狗屎铺就。而胜利没有臭味!为了这个值得忍耐。从我这方面可以保证: 老婆子的事再不会有了。咱们谈妥啦?”
“噢开—哎— 帕特里凯说咧!我睡觉去啦。” “我还得再工作一会儿 ......”
然而,我既没有睡成觉,也没能工作。夜里十二点二十分,奥 杜耶夫打来电话,要我立刻到他家去,他打算在家里搞一个罕见的诗歌之夜,要我一定带上“那个玩魔方的作家和长篇小说《杯酒人生》”。
“你怎么知道的呀?”
“全莫斯科都知道啦。我焦急地等着你!”我推醒维捷克,告诉他,我们去做客。
“你他妈的疯啦—在这个时候!”他一边骂,一边咧开大嘴打呵欠。
“作家们的生活才刚刚开始。习惯习惯吧!洗个淋浴去,你浑身都是洗衣粉 ......”
维克多摇摇晃晃地去了浴室,还不断撞到家具上。我看到他这 种酣睡不醒的状态,为防备万一,除了装着长篇小说的文件夹,把还剩一点“败德汤”的酒瓶子也塞进了皮包。
题图来自连续剧《战斗民族养成记》
(转自:小鸟与好奇心)
推荐文章
美股机会日报 | 凌晨3点!美联储将公布1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纳指期货涨近0.5%;13F大曝光!巴菲特连续三季减持苹果
美股机会日报 | 阿里发布千问3.5!性能媲美Gemini 3;马斯克称Cybercab将于4月开始生产
港股周报 | 中国大模型“春节档”打响!智谱周涨超138%;巨亏超230亿!美团周内重挫超10%
一周财经日历 | 港美股迎“春节+总统日”双假期!万亿零售巨头沃尔玛将发财报
从软件到房地产,美国多板块陷入AI恐慌抛售潮
Meta计划为智能眼镜添加人脸识别技术
危机四伏,市场却似乎毫不在意
财报前瞻 | 英伟达Q4财报放榜在即!高盛、瑞银预计将大超预期,两大关键催化将带来意外惊喜?